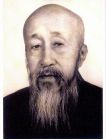沈钧儒:宪政救国的人权律师
2018-08-28 11:35:09
发表人:路人粉
作者惠赐|沈钧儒:宪政救国的人权律师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1875年生于江苏苏州。他于1904年,也即清朝废除科举制度的前一年,身入凤池,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进士。次年,沈钧儒东渡日本,求学于东京私立法政大学。1908年沈钧儒回国,历任浙江谘议局副议长、浙江省教育司司长、国会议员等职。1920年沈钧儒由司法部长徐傅霖颁发律师执业资格,1928年同其旧时上司张耀曾(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学士,前司法总长)等人合组律师事务所于上海。沈钧儒在律师界名望甚著,曾任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随国府迁渝后,又担任重庆律师公会主席。
看重法治价值,竭力保障人权
沈钧儒认为“国家颁设律师制度,其目的在扶持弱小,以保障人民之权益,辅助法院,以导纳社会于轨物。”他做律师,极为看重法治和人权。曾有富商请他代理讼案,手续办妥后,富商表示愿在律师公费之外另付两万元以作“运动”之用。沈钧儒因此拒绝受理此案。他说:“不讲法律而要运动,何必来找律师呢?”当时亦有报人记载:“他(即沈钧儒)办理诉讼案件,不像一般拜金主义者的律师,一切唯利是视。往往遇到贫穷者,他不收公费之外,还得贴出车马费和膳费。他经常勉励一般年轻的律师,要真正实践'保障人权’的任务,切不可媚富欺贫。”
沈钧儒办理了许多人权案件、政治案件。尤其在国民党清共期间,他代理辩护、设法营救诸多政治异见人士。有学者统计,仅1930-1935年之间,获其救援的便有19人之多。1935年5月,《新生》周刊刊登艾寒松文章《闲话皇帝》。日本驻上海领事认为该文“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政府追究文责。在日方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封《新生》周刊,逮捕主编杜重远,是为“新生事件”。事发后,作为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的沈钧儒会同陈霆锐、王惟桢向司法院呈文,为杜氏鸣冤。沈钧儒等认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乃商务官员,不能为国家之代表,因此根据《刑法》第119条和160条之规定,领事无权置喙此案;杜重远一审被判有罪后,本有权根据《刑事诉讼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而该案法院在一审之后即驳回杜氏之上诉,“至若一审而止,别无上诉救济之方,则实为按之现代文明各国司法制度,实无先例可以引援……影响法治前途至巨。”
念及清共期间冤案频发,沈钧儒决心“联合各界,一致促成政府完成冤狱赔偿法规,使与宪法同日施行,以健全国家之组织。”1933年,沈钧儒在中华民国律师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上提交了《本会应建议立法院制定冤狱赔偿法案》的提案。1935年,沈钧儒当选中华民国律师协会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主席,该会讨论了《冤狱赔偿法草案》,通过、发布了《冤狱赔偿运动工作大纲》和《冤狱赔偿宣言》。沈钧儒于1935、1936年内两次奔赴南京,推动《冤狱赔偿法》的制定和颁行。他实至名归地成为民国法制史上著名的“冤狱赔偿运动”的旗手。
组织爱国运动,身陷囹圄不悔
1930年代,中日局势急剧恶化,沈钧儒的爱国热情亦迸发一如电光火石。一日,他读到邹韬奋哀悼著名爱国报人戈公振的文章,悲愤之中作诗《我是中国人》,将其爱国之情宣泄如洪:
浙江古越国,勾践人中杰。尝胆卧则薪,我是浙江籍。
苏州有胥门,炯炯照双睛。怒视敌人入,我是苏州生。
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随着国难的加深,沈钧儒在律师职业外,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报纸上常常纪[记]载着他,总是做什么纪念会的主席或者示威游行的先导,他的年老的血,又在沸腾了。” 1931年至1932年,沈钧儒先后成为浙江省国难救济会、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上海各团体救国会联合会的发起人。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次年6月1日,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沈钧儒均被选为主席。
救国会运动的抗日主张与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的外交政策相左,日渐遭到国民政府的猜忌和打压。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运动领袖的风声逐渐流传,而沈钧儒却处之泰然。潘念之曾这样回忆这期间他俩的一次会面:
在他(沈钧儒)被捕的前一个月,在一家饭店中,又遇到了他,他告诉我,现在政府要逮捕他们,许多朋友劝他暂时避避。但是他说:“我不打算走,我准备着被捕,什么时候拘票送到,我就什么时候上法庭去。南京也好,上海也好,我都去得。现在正需要像我这样的老人来吃点亏,使大家可以激励一下。”
1936年11月,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因涉嫌危害民国罪遭到逮捕,是为“七君子”事件。在狱中,德高望重的沈钧儒被其他难友选为“家长”,继续组织、布置救国会事宜。为了营救“七君子”,上海律师精英们毅然挺身,陈霆锐(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律博士、原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江一平(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汪有龄(前司法次长、前朝阳大学校长)、江庸(前司法总长、朝阳大学校长)等21名沪上律师界的风云人物组成了强大的律师团,为其提供辩护。其中张耀曾、秦联奎(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和李肇甫(前国会议员)担任了沈钧儒的辩护律师。
经过律师团队和社会贤达的联手营救,沈钧儒等人于1938年7月28日被释放出狱。他在同年8月4日的一次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爱国的理由》,继续倡言爱国精神:
尊重个人自由,务使每一个人之言论行动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因有组织而获得其绝对之保障。这是群众所以要有国家,所以爱国的原因。到了整个国家被侵害被压迫的时候,我们便亦不得不牺牲其小我的一切,以争取其共同建立国家的自由。爱自己即所以爱国家,爱国家亦即所以爱自己。这是我们爱国一贯的理由。
追求宪政之梦,坚持宪政救国
作为法律人,沈钧儒的爱国之情不仅在于坚决抗战,更在于其对宪政的追求。早在1907年旅日期间,沈钧儒就加入了宪政讲习会,并与熊范舆等人联名向清廷呈交《民选议院请愿书》,主张立宪。沈钧儒等人主张:“国家成立,端赖法律以维持,世界之列强,均有一成之法典。中国疆域辽远,风俗各殊,朝廷既无一定之法文,民间又无共通之习惯,纷杂混乱,为世界所仅有,非使立法机关及早成立,必不能保国家之划一,而促社会之进步。”
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沈钧儒也没有在宪政问题上稍有松懈。他认为:
自从抗战以来,时代进展得太快了,因此,大家都觉得有提早实施宪政的必要,结束一党专政的政治,实施全民的民主政治,使各党各派都有参加政治的机会,以推动国内的政治,这已成为社会各方面共同迫切的要求了。
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团结抗战,组织了超越党派的国民参政会,实行宪政的主张在国民参政会中呼声很高。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等党派均有代表提出实施宪政的提案。作为国民参政员,沈钧儒亲身参与到国民参政会的宪政讨论之中,他也乐于将自己在国民参政会中的见闻同国民分享。沈钧儒曾发文记述:
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组里,对于实施宪政问题,曾有热烈的讨论,化[花]去时间不少,但无要领。于是,把它扩大讨论,所有各提案的参政员都参加讨论,亦无要领。最后,再把它扩大,只要热心宪政愿意参加该问题讨论的参政员都欢迎加入,从下午八时一直讨论到次日晨二时半,空气依然紧张热烈。在朝的党与在野的党,彼此间披沥肝胆,坦白挚诚,把要说的话,都赤裸裸地说出来了。尤其值得赞扬的,国民党朋友的话,都很切实中肯。辩论结果,觉得实施宪政,乃当前的急务,而结束党治,目前似乎不必特别强调,因为结束党治,乃实施宪政必然的程序。
经过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最后做出了“治标”、“治本”的两个决议。“治标”的,乃是“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大家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治本”的,则是“定期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
沈钧儒相信宪政是救国之路,因为“要建设新中国,宪法仿佛是打一个全部的具体的图样。……若是走上了宪政的路,就是走上了发展整个政治和平的积极的最正确的道路。”在宪政的实现上,他认为“宪法在世界有时被认为不祥之物,这是因为过去宪法多是人民向政府要求而得不到的缘故,人民需要宪法已至迫切,政府却无论如何不能准许,以致非革命不可。……宪法的产生必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人民热烈的要求,第二是政府诚意的接受。”因此,他主张“不论个人或国家在政治上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对于青年,他更是特别地嘱咐:“青年应当每逢国家要事,就自动负担起来,推进宪政运动,也是当前要务之一。”
奔走民主和平,反对政府暴政
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和谈成为最重要的议题。沈钧儒作为中间势力“民盟”的领袖奔走和平。和谈期间,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民盟事务上,以致自己的律师业务陷入停顿。《光明报》当时报道沈钧儒“常常是囊空如洗的,有几次连去南京的车票都是要史良先生帮忙。”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在未取得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识的情况下,单方面组织国民大会制宪。沈钧儒公开指责这一行为是“倒行逆施”,是“取消政协决议和恢复一党独裁的做法”,“丝毫不能解决问题”。面对采访,他向记者表示:“我们既不参加'国大’,又何必去讨论它呢?我对于报上的'宪草修正案’毫无兴趣,从来没有读过。”一向热衷宪政的沈钧儒作出这样的评论,可见其对这次“片面制宪”的失望与愤慨。
随着国共局势的紧张,国统区内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此起彼伏。为了稳固统治,上海等城市纷纷宣布戒严。沈钧儒对于戒严中侵犯人权和司法公正的情况十分不满。他撰写长文,对戒严政策提出批评:
近来“戒严”的恐怖,正弥漫着各重要城市,每个人的自由,都受着极重大的威胁,人们渴望着免于恐惧的自由,与渴望着免于饥饿的自由,同样的迫切。治安当局把“戒严”作为剥夺人权的利器,俨然无论在任何地域任何情况之下,随时随地都可以“戒严”,而实施了“戒严”之后,所有司法行政机关都失去了作用,军事机关权力更加澎涨[膨胀],对人民的非法逮捕、越权审理,以及所施的一切残暴行为,便都可以变为合法,“戒严”宣布之日,即人民权利丧失之时,这又是多么可怕的现象啊!
沈钧儒揭露各地戒严之后侵犯人权的恶行:“不问证据有无,不管违法与否,要侵入便侵入,要逮捕便逮捕,要殴打便殴打,甚至武汉大学军警架起机关枪,如临大敌,演成击毙学生惨剧”。他进而愤怒地追问:“胜利快两年了,人民得不到自由,得不到解放,所受到的是这非法的摧残与残暴的压迫,这样不讲法律,这样暗无天日,还谈什么人权?还说什么民主?!”
由于民盟与共产党的友好和对国民党的批评,国民党将民盟视为“中共之附庸”。1947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加以取缔,不久,沈钧儒被迫浮海前往香港。抵港后,沈钧儒等人重建民盟领导机关,召开一届三中全会,继续民盟的民主、宪政事业。1948年,沈钧儒发表《我对时局的看法》,表示:“真正的和平民主,要靠人民自己来争取。我们只有信赖人民力量到底,始终站在人民方面,一切问题才能解决。”次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沈钧儒和其他民主人士陆续来到北京。同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沈钧儒当选筹备会常务副主任,在政协的组织召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的当天,沈钧儒被任命为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此开始他的另一段法律生涯。